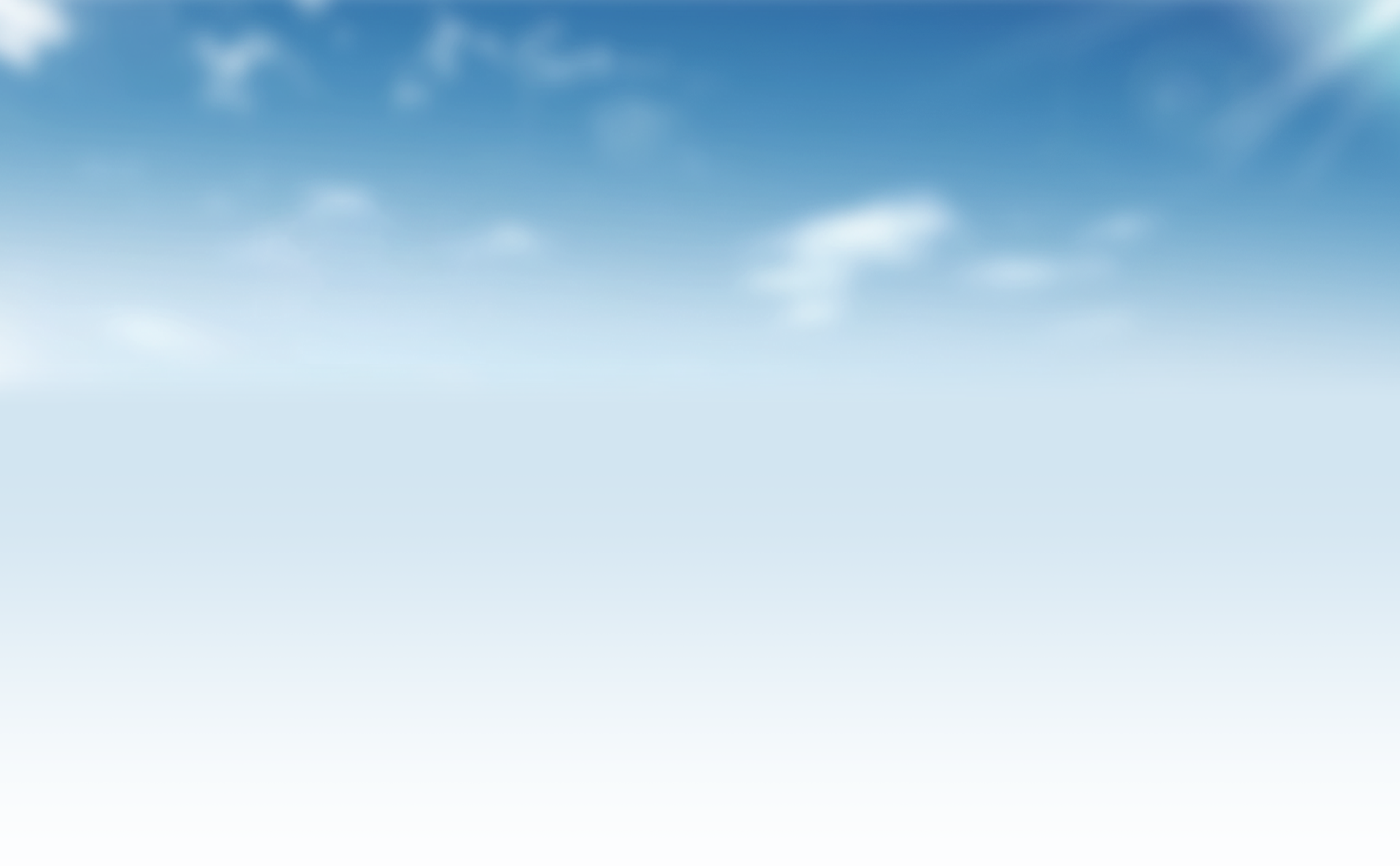中國一貫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並與時俱進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2024年1月,生態環境部發佈《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明確了我國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方向和重點任務。這是我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核心工具,是切實推進落實“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的國家行動,也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決策部署的重要舉措。
一、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形勢下的中國行動
生物多樣性持續喪失對人類福祉和生存造成了深遠影響,成為阻礙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風險。然而,至今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尚未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仍然面臨多重威脅。生物棲息地退化喪失、自然資源過度消費、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外來物種入侵等嚴重威脅著生物多樣性。我國作為最早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國家之一,1994年率先編制《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2010年《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發佈,提出未來2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總體目標、戰略任務和優先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逐步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全面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管理水準,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地位,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融入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明確新時期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新目標、新任務。2022年,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主席國,帶領各方達成“昆蒙框架”及所有配套政策措施,為未來十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擘畫新藍圖,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進程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
當前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推進全球環境治理的關鍵時期。《行動計劃》正式發佈,明確我國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部署、保護目標、優先領域和優先行動,引領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有助於改善我國生態環境,對塑造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體系起著關鍵作用。
二、新時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設定
2030年目標是《行動計劃》的核心目標,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政策、法規、制度、標準和監測體系基本建立,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得到有效緩解,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管理水準顯著提升,至少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退化生態系統得到有效恢復,以及利用遺傳資源和數字化序列資訊及其相關傳統知識所産生的惠益得到公正和公平分享等。《行動計劃》也明確了中長期目標與願景,即到2035年,形成統一有序、結構連通、動態調整的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空間格局,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可持續利用機制全面建立,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為公民自覺行動;到2050年,全面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願景。
《行動計劃》基於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引領者的新定位,緊密銜接“昆蒙框架”行動目標,將全球目標納入國家層面進行實施,設定符合國情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目標,激勵推動中國乃至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進程。《行動計劃》目標設定與國際履約需求有效融合。一方面是目標時間節點相呼應。《行動計劃》2030年目標與“昆蒙框架”2030年全球行動目標時間相呼應,中長期目標與願景的時間與“昆蒙框架”2050年全球長期目標時間相呼應,明確了不同時間階段中國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貢獻。另一方面是目標及行動領域相銜接。《行動計劃》2030年目標中包含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可持續利用與惠益共用和治理能力現代化4個優先行動目標,與“昆蒙框架”2030年全球行動目標,即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通過可持續利用和惠益分享滿足人類需求,及執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相銜接,其中《行動計劃》2030年目標中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為豐富地拓展了“昆蒙框架”中執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的2030年行動目標。
三、新時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行動
1.加快建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長效機制
從“昆蒙框架”到《行動計劃》,完善生物多樣性相關政策法規體系、建立長效機制都是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關鍵行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及環境保護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主流的過程,完善生物多樣性政策法規、體制機制和規劃計劃等,通過建立長效機制才能確保各行各業及各類群體始終將生物多樣性放在主要地位。同時,生物多樣性保護長效機制將預防生物多樣性破壞行為,推進源頭管控,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同步,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由國家戰略轉化為具體實踐,保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
鋻於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系統性、長期性,建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長效機制尤為迫切,應加快推進以下工作:一是加快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建設,持續推進生物多樣性相關領域法律法規制定修訂工作,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及制度體系,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二是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協同治理機制,推進國家與地方、政府多部門間協同聯動機制,強化各級政府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主導作用;三是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及其多重價值觀持續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和相關部門的行業中長期發展規劃、工作計劃及有關行動方案等;四是出臺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全民行動方案。
2.加強就地保護監管與協同治理
加強就地保護監管與協同治理修復受損生態系統是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迫切需要。生物多樣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為人類社會提供了衣、食、住、行及文化生活,是綠色發展的基礎和支撐。加強就地保護監管是守護生物多樣性原生境最重要的途徑。同時,應減少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因素,協同治理修復受損生態系統,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局面,以築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基礎。
為進一步加強監管和推進協同治理,應重點關注以下方面:一是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加強對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等保護監督,優化海洋生態安全格局;二是開展生態恢復重點區域識別與判定,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三是採取近自然工程措施開展棲息地修復和生態廊道建設;四是協同推進減污、降碳、擴綠、增長,統籌制定生物多樣性適應氣候變化政策框架等。
3.積極推動可持續利用與惠益共用
探索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推動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與惠益共用是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路徑。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重要基礎,而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有助於地方形成自生動力維護生物多樣性,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社會經濟穩態發展的雙贏局面。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惠及整個社會,事關國家生態安全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路徑。
為加快推進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行動計劃》也明確了以下重點任務:一是強化國家層面種質資源利用平臺和共用體系建設,加強生物遺傳資源資訊管理,開展生物多樣性相關農牧、醫藥、傳統文藝、民俗技藝等傳統知識調查編目與評估;二是依託自然承載力統籌山區、平原、林區、海島等區域的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通過生態涵養、現代農業、全域旅遊、科技創新等不同發展定位推動生態産業化和産業生態化,強化生物多樣性在相關行業和領域的可持續利用;三是應堅持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部署,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升級。
4.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
系統構建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對提高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管理水準至關重要。目前,中國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仍處於發展階段,全方位提升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將能更有效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威脅,有助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彰顯中國智慧。
有效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應著力加快以下行動。一是提升與社會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力,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設備研發與國際接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資訊化和現代化建設;二是積極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參與生物多樣性相關國際標準制定,加強關鍵議題的交流磋商;三是充分發揮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的作用,積極推進生物多樣性國際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提升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的能力,匯集各方力量共同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挑戰。
四、完善工作協調機制,保障行動落地
工作協調機制是落實好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與行動的重要保障,應圍繞各項行動的組織實施、完善投融資機制及強化技術支撐等形成《行動計劃》實施的保障體系。
一是加強組織領導落實各方責任。建立統籌推進《行動計劃》的工作機制,細化部署任務分工和實施方案,各相關部門履行好生物多樣性保護職責,加強統籌協調,推動工作落實,進行跟蹤評估和監督檢查,形成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完善隊伍建設和資金保障機制。建設高素質專業化隊伍和科技人才團隊,引進生物多樣性保護急需的管理和技術人才,建立地方生物多樣性保護專家庫。加強各級財政資源統籌繼續支援生物多樣性保護,構建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多渠道、多領域籌集保護資金。
三是強化技術支撐系統研究關鍵領域。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保護科研平臺和基地,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標準化技術支撐工作,科學研判生物多樣性治理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問題,科學支撐重大方針政策、決策部署,積極參與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交流合作。
(作者係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文明中心首席科學家、研究員 張惠遠,研究室主任、高級工程師 齊月,助理研究員 秦樂)